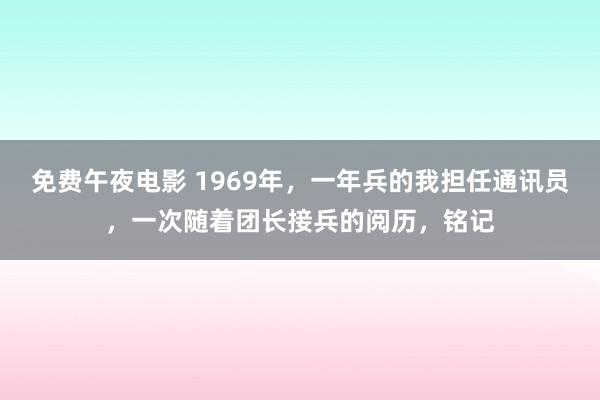
"你说你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员?讲授呢?泰深宵的免费午夜电影,谁知说念你是不是冒充的!"值班员手电筒的光晃得我睁不开眼,那声息里带着完全的警惕。
那是1969年的盛夏,我还清纯洁白谨记那天的闷热,像是悉数这个词东说念主泡在了滚水缸里。
电线杆上的蝉鸣一浪高过一浪,嗡嗡动掸的风扇也赶不走这股子闷热劲儿。
我叫李长河,能当上团长通讯员老到气运,要不是会打字,指不定当今还在连队擦枪呢。
那会儿我在新兵连,整天除了磨练即是擦枪,擦得枪管子都能照见东说念主影。
战友们都见笑我这东说念主痴钝,话语大喘息:"老李啊,你这形貌去站岗,准能把敌东说念主给憋走。"
可我就这样个挨次,打字贼快。还谨记新兵联贯业那天,团长王建军来队里调查,正排场见我在打字机上帮指示员誊写论述。
那打字机是老古董了,可在我手下面,那叮叮当当的声息听着特别悠然。
团长就这样把我要去当了通讯员,从此我的军旅生涯就变了个样。
团长是个扬铃打饱读的东说念主,里通外国,寰球都叫他"钢铁团长"。
张开剩余84%可要说他对战士们的体恤,那是真认知切的,一丝一滴都记在心里。
谨记有次他看见一个战士吃饭没胃口,二话没说就把东说念主送到病院查验,自后发现是阑尾炎,实时手术这才没犹豫大事。
那天晚上的事儿,当今想起来还以为可笑。我正睡得跟死猪似的,被子都踢到地上了。
值班员一把把我摇醒:"团长找你!"我一骨碌爬起来,裤子都来不足扣好就往外跑。
团部的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下,团长在屋里走来走去,那背影显得特别广大。
"小李,打理东西,跟我去火车站接新兵!"说着递给我一沓名单,那会儿的名单都是用钢板刻印的,油墨味儿大哥。
谁知说念中途上,团长倏得接到电话,说师里有要害会议。
他拍拍我肩膀:"你先去,我开完会就到。对了,新兵档案袋在我车上。"说完就急遽走了。
那会儿的火车站哪有当今这样敞亮,就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照得东说念主影绰绰的。
值班员老张刚从边防调过来,纯情学生妹厚爱得很,非要看证件。偏巧我这证件落寝室了,这下可把我给愁坏了。
r级书屋春色吧"同道,我的确团里的通讯员,你看我这独处孤身一人军装......"
"军装?呵,谁还不会穿件军装啊!"老张的声息里带着几分讪笑。
就在我急得直顿脚的时刻,月台上传来汽笛声。远瞭望去,一列绿皮火车迟缓驶来,车厢里都是新兵的身影。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但是大事啊,若是真犹豫了接新兵,我这通讯员也甭干了。
正在这节骨眼上,团长的声息在背后响起:"老张,他是我们团的李长河,确乎是我派来的。"
我这才松了语气,团长来得的确时刻,要否则我今晚就得在值班室里蹲着了。
月台上的情状,这样多年曩昔了还绝无仅有在目。特别是阿谁站在边缘抹眼泪的新兵张德民,那身影老是时时在我梦里出现。
"你叫啥名字?"团长走曩昔问说念。
"论述团长,我叫张德民。"那小伙子抽抽噎搭地说,眼泪在蟾光下闪着光。
我寻想,这娃娃看着挺结子,咋这样爱哭呢?谁知说念他的故事比我设想的要千里重得多。
原来他爹得了重病,家里就他一个女儿。那会儿农村老庶民看病难,吃饭都是问题。
他妹妹才十二岁,上学的钱都凑不都,整寰球学后就去地里捡柴火。
听完张德民的诉说,团长千里默了好瞬息。蟾光下,我看见团长的眼睛湿润了。
"这样,你先跟小李且归望望你爹,我让别的同道送新兵回营。"团长的声息里带着深深的疼惜。
我跟张德民坐上了去他家的班车。一齐上,他给我讲他们村的事。
村里依然好几年没出过参军的了,此次他能参军,全村东说念主都为他欢笑,还专门杀了只鸡给他送行。
可他爹前些日子在地里干活我晕了,到当今还没缓给力来。大夫说是累的,可谁知说念是不是有啥大罪恶。
他们家在山沟沟最里头,连个像样的路都莫得。下了班车还得走仨弯子。
蟾光下,土坯房歪七扭八的,像是随时会倒。院子里堆着些干柴,想必是他妹妹捡的。
屋里点着煤油灯,张父躺在木板床上,床边放着个破旧的暖水瓶,内部的水早就凉了。
见女儿来了,老东说念主家强迫支起身子:"德民,你咋总结了?"那声息败北得很,可照旧掩不住慷慨。
"爹......"张德民刚启齿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参军是功德啊!你爷爷辞世的时刻总念叨,咱家就盼着能出个军东说念主。你若是因为我退了伍,我这心里过不去!"
张父的声息固然败北,可字字明晰,那股子倔劲儿让东说念主心里发酸。
张德民的妹妹站在门边,抹着眼泪。我广阔到她的布鞋都表示了脚趾头,裙子上打着好几个补丁。
那一刻,我倏得明显了什么叫军东说念主的包袱,什么叫家国情愫。
回到队列后,我把情况原正本腹地论述给了团长。谁知说念团长早就作念了安排。
他让卫生队的医师轮替去给张父看病,还把张德民妹妹的膏火给处理了。
这事在队列里传开后,战士们纷繁捐钱。有的把零费钱都掏出来了,有的把家里寄来的钱也捐了。
谨记有个战士说:"咱参军的是一家东说念主,有难处寰球襄理着点。"这话说得朴实,可字字都暖到心里。
张德民自后成了我们团的尖兵,还被评为"学雷锋尖兵"。每次见到他,我都能从他意见中看到那份对队列的深深留恋。
他常说:"要不是队列,我爹可能早就不在了。这身军装,我得穿出个形貌来。"
特意旨兴致的是,几年后张德民和卫生队阿谁庸碌去给他爹看病的女照管程丽处对象了。
那小姐叫程丽,本性顺心,庸碌给张父熬中药,自后就这样走到一齐了。
团长还当了他们的证婚东说念主,那是我头一次看见团长笑得这样欢快,像是自家妮儿许配似的。
日子就这样曩昔了,我也成了个老兵。当今队列条款好了,可我总以为那会儿的战友情更地说念。
每到深宵东说念主静,我就会想起阿谁站台上抹眼泪的大小伙,想起那间破旧的土屋,想起战友们捐钱时的情状。
阿谁盛夏的故事,就像一杯老酒,越品越醇。它让我明显,什么是舍小家为寰球,什么是军东说念主的担当,更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当时的蟾光,那份战友情,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我的驰念里,历久抹不去。
就像那年夏天的蝉鸣,远远地传来免费午夜电影,又远远地去了,可那份厚谊,却历久留在了心底。
发布于:黑龙江省